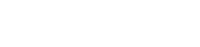而夏秋华,被谢绮一番话噎得发懵,却还是强撑着扬起下巴,一如既往地摆出那副“我委屈但我不说”的架势。她嗓音发紧,却故意装得倔强坚定:“谢小姐,我知道你和蛮蛮交好,从来都看我不顺眼。”“你现在这般说我,无非是为了帮她把我从伯父家赶出去罢了。”
她抬眸看着谢绮,眼中隐隐含泪,声音也压得低低的:“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说了几句实话,至于吗?何必这么对我说话。”谢绮闻言气笑了,步子往前一迈,双手抱胸,毫不客气地冷笑出声:“你这招还不腻吗?我不管你怎么在别人面前装,在我面前少来那一套”谢绮说完,眸光横过去,看了眼仍不出声的谢知止。她一字一顿,咬牙道:“表哥,她今天敢在你面前污蔑蛮蛮,明天就敢拿着你的名字去别处邀功。”
谢知止终于开口说话:夏姑娘,尽管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何矛盾,既然你说蛮蛮和你说了我,不如等见到蛮蛮我们对峙一番就知道真假了。
夏秋华脸色骤然一僵。她下意识抿紧了唇,眼神里掠过一丝短暂的慌乱。她不是没和人当面对峙过,以往不论是下人还是同辈,只要她委屈地一低头,软声软气几句“蛮蛮不喜欢我”十有八九都能让人偏向自己。毕竟她和蛮蛮同吃同住,是堂姐妹,别人会误以为她们关系好,再加上蛮蛮性子平时也任性、懒得去讨好别人,所以夏秋华从不怕硬碰。但这一次——她真的有些慌了。
谢绮见此冷哼一声:“哼,做贼心虚”所有人都在等谢知止回应。可他只是微微偏了偏头,似乎在思索,又似乎并未听得太入心。他一贯的温和脸色并无太多变化,只是唇角微敛,语气仍是那样从容:“旁人言语真假,于我无碍,是非真假,我心中自有判断,绮绮表妹也不可再咄咄逼人”谢知止说完,便不再看夏秋华,也不看任何人,只抬步继续挑马,目光落在马场尽头那匹青鬃烈马上,神色寡淡。
谢绮站在原地,脸色难看得几乎要炸开,手指死死攥着衣角,气得直跺脚,却拿他一贯的冷淡无措。夏秋华则彻底僵在原地。不远处的树丛后,蛮蛮依旧静静站着,面色冷淡,半点没有先前那种爱笑的娇俏模样。她没哭,也没气,只是眼神一点点沉下去。夏秋华,果然还是那个夏秋华。手段依旧,拙劣依旧,不堪依旧。她看着远处谢知止的背影,眸光一瞬微动,却很快收回。就在这时,一只手悄悄搭上了她的肩。
往生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将她搂进怀里,另一只手稳稳地抚着她的背,一下一下,像是在哄一只被惊扰的小兽。蛮蛮终于低头,回头看向他。她看着往生眼底的坚定,那种不掺杂任何迟疑的“站在她身边”的信号。她忽然意识到,除了谢绮,能完全站在自己身边不搭理夏秋华的竟只有往生。其他人或许心里明白,却因为太多牵扯、太多关系,始终不愿为她落下真切的一个“立场”。都是嘴上说着小姑娘矛盾,夏秋华可怜,让蛮蛮别过多计较,如果蛮蛮非要计较,就要说蛮蛮任性不饶人了。
这世道就是如此,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是非分明。可往生不是那样的他一向沉默寡言,从不争辩,但每一次她被逼到绝境,他总会默默站在她身后,像一株静静护她的树,替她挡风遮雨。此时往生的清朗声音在耳边响起来:“蛮蛮,别难过。我永远会相信你的话。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哥哥都会信你、帮你。”
蛮蛮猛地转身抱住他,脸贴在他肩头,深深嗅着那熟悉的味道,佛手的清香与甘松的草木香交织在一起,会让她感觉格外的安稳。亲情是蛮蛮早已放弃的东西,在蛮蛮心中只要有人这样永远无条件的偏爱自己,相信自己坚定的选择自己一个人那就够了,无论谁都可以。
蛮蛮抱着往生静默了一会,像是汲取了片刻温暖,才慢慢退出他的怀抱。她低头抚了抚袖子上的褶皱,语气轻轻的,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清明:“我猜她一会儿还得闹,等着看吧,宴会上又该玩什么花样。”她顿了顿,抬眼看向不远处灯火未明的方向,神色淡淡:“只可惜这是京城,不像在师门那样,我能直接动手。这里讲究身份、讲究体面,没有足够的权势,手段再多也不好使。”她轻轻一笑,痛恨权势却要倚偎权势,眼底渐冷:“所以啊……我得不惜代价,把谢知止勾到手,让他迟早有一天会来求我,真想看看他哭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蛮蛮与往生在马场分开后,因为男女宴会分开的所以独自一人回了宴会。她特意选了个离母亲不远不近的位置坐下,既方便母亲随时唤她,又不会显得刻意亲近。她一边慢条斯理地剥着果子皮,一边淡淡扫视四周。没过多久,她就看见夏秋华踩着裙摆朝这边走来,眼神里带着点子算计与得意。蛮蛮勾了勾唇角,心中早有预感,这位堂姐一向按捺不住,今日必定还要再折腾点什么出来。
果不其然,等到宴会将尽,宾客纷纷举杯准备辞席之时,王夫人便带着夏云氏和夏秋华,一起往谢家那边的座位走了过去,满面笑容地与谢家祖母和谢夫人寒暄起来。蛮蛮一手撑着下巴,远远望着那边,果然看见夏秋华笑得温婉殷勤,却眉眼中藏着些藏不住的心机。就在她话说到一半时,旁侧忽然传来一声轻笑,宛若银铃却冷意十足。
“母亲,你看吧,我就知道她又要来祖母和伯母面前搬弄是非了。”说话的是谢绮跟在谢凌灵的手从夏秋华背后走来,夏秋华没料到她们会突然出现,脸色当即一僵。谢凌灵却立即低声呵斥谢绮:“没规矩,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在外头怎么就这么口无遮拦。”语气不轻,但落在旁人耳中,却分明不是要真的训谢绮。谢绮被呵斥后,也没半点惧色,反倒往母亲身边靠了靠,语气一如既往的娇:“我就是实话实说嘛,母亲最不喜欢别人背后挑拨是非了。谢家家规不是也这样规定了嘛”
说完王夫人脸色立马变了,谢家祖母没有声色,但是谢家主母-谢凌灵眼底有一丝轻蔑和鄙夷,从刚才夏秋华张嘴开始其实那一丝轻蔑就存在了,谢家身为百年世族,最讲究的便是“分寸”二字,要谨言慎行,更遑论女眷间言语失仪,口舌是非更是家族大忌,口舌之争,是下人之举,试图借言语挑拨、攀附的举动,在谢家看来,不啻于当众出丑。
更何况谢夫人身为当家祖母,坐镇中馈多年,什么样的心思没见过?一个人眼中几分真意、几分算计,她瞥一眼便知。夏秋华满眼算计,这等小心机、小伎俩,根本上不了台面。借机搬弄是非,借势打压族中弟妹,手段不仅低劣,且拙得发笑。一个晚辈,竟还敢借她之手挑唆离间使手段,实在不知礼数为何物。心眼还敢玩到她头上来,也不掂量掂量分量。谢夫人眼底波澜不兴,心中已然轻判。到底出身不同,看事、行事,都透着一股寒酸气。
甚至不免疑惑:夏家怎会如此愚钝,竟让一个非亲生的女儿在这种场合出头张扬,搬弄口舌?
送上门来丢人现眼。尽管对夏家一些做法早有耳闻但是还是无法理解夏家自以为亏待自己的孩子,去厚待别人的孩子来凸显自己仁德宽厚的做法。
一旁的王夫人人精似的,不禁也有些埋怨夏云氏平时她心下也不禁懊恼起夏云氏来,平日里耳边听得尽是她夸什么秋华懂事听话、端庄稳重,又说蛮蛮如何任性难教。她起初也信了几分,以为是蛮蛮从小离家游历,和她不亲近难免有几分隔阂,哪知今日一见,倒觉得这姑娘眼神透着股不安分和算计。当时她还以为不过是小女儿家的敏感要强,不曾想竟是这样小家子气,场面都撑不住,还差点连累了她这个引路人。
谢家女眷一个比一个沉得住气,偏生她们一句话不说,反倒叫她脸上也挂不住。她心念一转,赶忙笑着接话,打圆场道:“咳,小孩子年纪还小,话是快了些,倒也是一片热忱,怪她不得。如今正好大家都在,我替她赔个不是,权作个教训。”说着,还朝谢家祖母、谢夫人那边微微俯身,态度恭敬得很。
夏秋华这个时候哪还能不明白自己是什么处境?谢家女眷虽未明说,可那份冷意与轻蔑早就写在眼底。可她一如既往,倔得不肯低头哪有一句道歉?就像从前一样。
那还是她们年幼时,有一次她与蛮蛮、另一位表姐在园中一同玩耍。玩着玩着,夏秋华忽然扯着嘴角坏笑了一下,凑到蛮蛮耳边说:“我就跟表姐说你刚才说她坏话了,看她会不会气你。”说完这句话,她竟真的转身就跑去表姐身边,拉着人家嘀嘀咕咕说个不停。那时的蛮蛮年纪还小,乍一见那情形,吓得连忙跑过去辩解:“我没有,我什么都没说。”可她话还没说完,那个表姐便哭着跑去找了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蛮蛮的姑母告状去了。等姑母气冲冲赶来时,蛮蛮只来得及说一句“不是我”,便被劈头盖脸一顿斥责。
她母亲在一旁听了,不但没替她说一句话也不听她解释,反倒跟着一起责骂。那日的鞭子是打在院子里当众落下的。衣角被扯裂了,膝盖跪得红肿,耳边全是那句:“小小年纪就管不好自己的嘴,还竟敢不欢迎姑母,轮着你说什么事情”蛮蛮记得那天的阳光特别亮,落在廊檐下,晃得人眼疼。
后还是因为蛮蛮死也不认错、不道歉,才逼得姑母起了疑心,将表姐拉到旁边屋里单独问话。
没过多久,她又将蛮蛮与夏秋华一同叫了进去,分开对峙。那时候夏秋华也还年幼,虽嘴硬,但到底扛不住大人的威压,终于露出口风,说了实话。可让蛮蛮最难过的不是事情被查清,而是在真相面前,她依旧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长辈的保护与道歉。夏秋华听见众人识破她的心思,反倒梗着脖子、涨红了脸,咬着牙喊道:“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我不喜欢她!”
那句话,她记得很清楚。一句“我不喜欢她”,让一个孩子能心安理得地做出陷害同辈的事,还不觉得羞耻,甚至理直气壮。而她没有被骂,甚至没有被呵斥。之前一声不吭的祖母这个时候反而劝说“这孩子亲娘跟着别人跑了不管她,自小没人管教,也是可怜。”因为生怕夏秋华因此被蛮蛮的父亲赶出门不替大儿子养着。
就这样,一句“可怜”,轻轻地抹去了对错。仿佛她所有的狠、恶、阴毒,都能因为“没娘”二字被理解,被原谅。可那天跪在地上的蛮蛮呢?她只因不肯认下一个莫须有的错,便被生生打了半炷香,衣角血迹斑驳,掌心磨破,连一句“你委屈了”都没有听见。
蛮蛮从回忆里慢慢回过神来。眼前仍是那个熟悉的侧脸——夏秋华仿佛永远都那样,挺着脖子,嘴唇紧抿着,一副永不低头的模样。哪怕局势已变,众人眼神尽数落在她身上,她也还是那副傲气的样子,仿佛谁也奈何不了她。蛮蛮只是淡淡地望着,神色平静无波。
那副模样,反倒显得她像个旁观者,仿佛刚才被挑衅的人从来不是她。王夫人到底还是懂场面的,面色讪讪地站起来,低声扯了扯夏云氏的袖子,转身将母女俩带离了谢家席前。一场尴尬的戏终被强行收场。谢家祖母依旧稳坐原位,未出一言,只抿了口茶,便将目光移向别处。谢夫人与谢凌灵相视一眼,也未多言,只顺势与旁边的夫人们攀谈起来,话题很快便转到哪个世家新出的笛曲、哪家的表姑娘近日要下嫁何处,一如既往,体面、有分寸、不留余地。没人再提王夫人,也没人回头看那母女俩一眼。
至此,蛮蛮知道这场宴席之后,谢家女眷不再给她留面子,连王夫人都没能再多留半分情分,夏秋华这条路,算是走到了尽头。而蛮蛮,也终于在心底悄然划下一笔账:这一局,她赢了。她站起身时步态从容,裙摆掠过花纹青石,细细擦着余光未散的暮色,只转身悄悄去了谢绮的帐篷外。她站在帐前等着,不多时,便有丫鬟提灯而来将谢知止的批注交给她。
蛮蛮点点头,神色极安静,她低头拨了拨袖间细线,眼尾却带着笑意。接下来,就该轮到她自己登场了。
她抬眸看着谢绮,眼中隐隐含泪,声音也压得低低的:“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说了几句实话,至于吗?何必这么对我说话。”谢绮闻言气笑了,步子往前一迈,双手抱胸,毫不客气地冷笑出声:“你这招还不腻吗?我不管你怎么在别人面前装,在我面前少来那一套”谢绮说完,眸光横过去,看了眼仍不出声的谢知止。她一字一顿,咬牙道:“表哥,她今天敢在你面前污蔑蛮蛮,明天就敢拿着你的名字去别处邀功。”
谢知止终于开口说话:夏姑娘,尽管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何矛盾,既然你说蛮蛮和你说了我,不如等见到蛮蛮我们对峙一番就知道真假了。
夏秋华脸色骤然一僵。她下意识抿紧了唇,眼神里掠过一丝短暂的慌乱。她不是没和人当面对峙过,以往不论是下人还是同辈,只要她委屈地一低头,软声软气几句“蛮蛮不喜欢我”十有八九都能让人偏向自己。毕竟她和蛮蛮同吃同住,是堂姐妹,别人会误以为她们关系好,再加上蛮蛮性子平时也任性、懒得去讨好别人,所以夏秋华从不怕硬碰。但这一次——她真的有些慌了。
谢绮见此冷哼一声:“哼,做贼心虚”所有人都在等谢知止回应。可他只是微微偏了偏头,似乎在思索,又似乎并未听得太入心。他一贯的温和脸色并无太多变化,只是唇角微敛,语气仍是那样从容:“旁人言语真假,于我无碍,是非真假,我心中自有判断,绮绮表妹也不可再咄咄逼人”谢知止说完,便不再看夏秋华,也不看任何人,只抬步继续挑马,目光落在马场尽头那匹青鬃烈马上,神色寡淡。
谢绮站在原地,脸色难看得几乎要炸开,手指死死攥着衣角,气得直跺脚,却拿他一贯的冷淡无措。夏秋华则彻底僵在原地。不远处的树丛后,蛮蛮依旧静静站着,面色冷淡,半点没有先前那种爱笑的娇俏模样。她没哭,也没气,只是眼神一点点沉下去。夏秋华,果然还是那个夏秋华。手段依旧,拙劣依旧,不堪依旧。她看着远处谢知止的背影,眸光一瞬微动,却很快收回。就在这时,一只手悄悄搭上了她的肩。
往生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将她搂进怀里,另一只手稳稳地抚着她的背,一下一下,像是在哄一只被惊扰的小兽。蛮蛮终于低头,回头看向他。她看着往生眼底的坚定,那种不掺杂任何迟疑的“站在她身边”的信号。她忽然意识到,除了谢绮,能完全站在自己身边不搭理夏秋华的竟只有往生。其他人或许心里明白,却因为太多牵扯、太多关系,始终不愿为她落下真切的一个“立场”。都是嘴上说着小姑娘矛盾,夏秋华可怜,让蛮蛮别过多计较,如果蛮蛮非要计较,就要说蛮蛮任性不饶人了。
这世道就是如此,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是非分明。可往生不是那样的他一向沉默寡言,从不争辩,但每一次她被逼到绝境,他总会默默站在她身后,像一株静静护她的树,替她挡风遮雨。此时往生的清朗声音在耳边响起来:“蛮蛮,别难过。我永远会相信你的话。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哥哥都会信你、帮你。”
蛮蛮猛地转身抱住他,脸贴在他肩头,深深嗅着那熟悉的味道,佛手的清香与甘松的草木香交织在一起,会让她感觉格外的安稳。亲情是蛮蛮早已放弃的东西,在蛮蛮心中只要有人这样永远无条件的偏爱自己,相信自己坚定的选择自己一个人那就够了,无论谁都可以。
蛮蛮抱着往生静默了一会,像是汲取了片刻温暖,才慢慢退出他的怀抱。她低头抚了抚袖子上的褶皱,语气轻轻的,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清明:“我猜她一会儿还得闹,等着看吧,宴会上又该玩什么花样。”她顿了顿,抬眼看向不远处灯火未明的方向,神色淡淡:“只可惜这是京城,不像在师门那样,我能直接动手。这里讲究身份、讲究体面,没有足够的权势,手段再多也不好使。”她轻轻一笑,痛恨权势却要倚偎权势,眼底渐冷:“所以啊……我得不惜代价,把谢知止勾到手,让他迟早有一天会来求我,真想看看他哭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蛮蛮与往生在马场分开后,因为男女宴会分开的所以独自一人回了宴会。她特意选了个离母亲不远不近的位置坐下,既方便母亲随时唤她,又不会显得刻意亲近。她一边慢条斯理地剥着果子皮,一边淡淡扫视四周。没过多久,她就看见夏秋华踩着裙摆朝这边走来,眼神里带着点子算计与得意。蛮蛮勾了勾唇角,心中早有预感,这位堂姐一向按捺不住,今日必定还要再折腾点什么出来。
果不其然,等到宴会将尽,宾客纷纷举杯准备辞席之时,王夫人便带着夏云氏和夏秋华,一起往谢家那边的座位走了过去,满面笑容地与谢家祖母和谢夫人寒暄起来。蛮蛮一手撑着下巴,远远望着那边,果然看见夏秋华笑得温婉殷勤,却眉眼中藏着些藏不住的心机。就在她话说到一半时,旁侧忽然传来一声轻笑,宛若银铃却冷意十足。
“母亲,你看吧,我就知道她又要来祖母和伯母面前搬弄是非了。”说话的是谢绮跟在谢凌灵的手从夏秋华背后走来,夏秋华没料到她们会突然出现,脸色当即一僵。谢凌灵却立即低声呵斥谢绮:“没规矩,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在外头怎么就这么口无遮拦。”语气不轻,但落在旁人耳中,却分明不是要真的训谢绮。谢绮被呵斥后,也没半点惧色,反倒往母亲身边靠了靠,语气一如既往的娇:“我就是实话实说嘛,母亲最不喜欢别人背后挑拨是非了。谢家家规不是也这样规定了嘛”
说完王夫人脸色立马变了,谢家祖母没有声色,但是谢家主母-谢凌灵眼底有一丝轻蔑和鄙夷,从刚才夏秋华张嘴开始其实那一丝轻蔑就存在了,谢家身为百年世族,最讲究的便是“分寸”二字,要谨言慎行,更遑论女眷间言语失仪,口舌是非更是家族大忌,口舌之争,是下人之举,试图借言语挑拨、攀附的举动,在谢家看来,不啻于当众出丑。
更何况谢夫人身为当家祖母,坐镇中馈多年,什么样的心思没见过?一个人眼中几分真意、几分算计,她瞥一眼便知。夏秋华满眼算计,这等小心机、小伎俩,根本上不了台面。借机搬弄是非,借势打压族中弟妹,手段不仅低劣,且拙得发笑。一个晚辈,竟还敢借她之手挑唆离间使手段,实在不知礼数为何物。心眼还敢玩到她头上来,也不掂量掂量分量。谢夫人眼底波澜不兴,心中已然轻判。到底出身不同,看事、行事,都透着一股寒酸气。
甚至不免疑惑:夏家怎会如此愚钝,竟让一个非亲生的女儿在这种场合出头张扬,搬弄口舌?
送上门来丢人现眼。尽管对夏家一些做法早有耳闻但是还是无法理解夏家自以为亏待自己的孩子,去厚待别人的孩子来凸显自己仁德宽厚的做法。
一旁的王夫人人精似的,不禁也有些埋怨夏云氏平时她心下也不禁懊恼起夏云氏来,平日里耳边听得尽是她夸什么秋华懂事听话、端庄稳重,又说蛮蛮如何任性难教。她起初也信了几分,以为是蛮蛮从小离家游历,和她不亲近难免有几分隔阂,哪知今日一见,倒觉得这姑娘眼神透着股不安分和算计。当时她还以为不过是小女儿家的敏感要强,不曾想竟是这样小家子气,场面都撑不住,还差点连累了她这个引路人。
谢家女眷一个比一个沉得住气,偏生她们一句话不说,反倒叫她脸上也挂不住。她心念一转,赶忙笑着接话,打圆场道:“咳,小孩子年纪还小,话是快了些,倒也是一片热忱,怪她不得。如今正好大家都在,我替她赔个不是,权作个教训。”说着,还朝谢家祖母、谢夫人那边微微俯身,态度恭敬得很。
夏秋华这个时候哪还能不明白自己是什么处境?谢家女眷虽未明说,可那份冷意与轻蔑早就写在眼底。可她一如既往,倔得不肯低头哪有一句道歉?就像从前一样。
那还是她们年幼时,有一次她与蛮蛮、另一位表姐在园中一同玩耍。玩着玩着,夏秋华忽然扯着嘴角坏笑了一下,凑到蛮蛮耳边说:“我就跟表姐说你刚才说她坏话了,看她会不会气你。”说完这句话,她竟真的转身就跑去表姐身边,拉着人家嘀嘀咕咕说个不停。那时的蛮蛮年纪还小,乍一见那情形,吓得连忙跑过去辩解:“我没有,我什么都没说。”可她话还没说完,那个表姐便哭着跑去找了自己的母亲,也就是蛮蛮的姑母告状去了。等姑母气冲冲赶来时,蛮蛮只来得及说一句“不是我”,便被劈头盖脸一顿斥责。
她母亲在一旁听了,不但没替她说一句话也不听她解释,反倒跟着一起责骂。那日的鞭子是打在院子里当众落下的。衣角被扯裂了,膝盖跪得红肿,耳边全是那句:“小小年纪就管不好自己的嘴,还竟敢不欢迎姑母,轮着你说什么事情”蛮蛮记得那天的阳光特别亮,落在廊檐下,晃得人眼疼。
后还是因为蛮蛮死也不认错、不道歉,才逼得姑母起了疑心,将表姐拉到旁边屋里单独问话。
没过多久,她又将蛮蛮与夏秋华一同叫了进去,分开对峙。那时候夏秋华也还年幼,虽嘴硬,但到底扛不住大人的威压,终于露出口风,说了实话。可让蛮蛮最难过的不是事情被查清,而是在真相面前,她依旧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长辈的保护与道歉。夏秋华听见众人识破她的心思,反倒梗着脖子、涨红了脸,咬着牙喊道:“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我不喜欢她!”
那句话,她记得很清楚。一句“我不喜欢她”,让一个孩子能心安理得地做出陷害同辈的事,还不觉得羞耻,甚至理直气壮。而她没有被骂,甚至没有被呵斥。之前一声不吭的祖母这个时候反而劝说“这孩子亲娘跟着别人跑了不管她,自小没人管教,也是可怜。”因为生怕夏秋华因此被蛮蛮的父亲赶出门不替大儿子养着。
就这样,一句“可怜”,轻轻地抹去了对错。仿佛她所有的狠、恶、阴毒,都能因为“没娘”二字被理解,被原谅。可那天跪在地上的蛮蛮呢?她只因不肯认下一个莫须有的错,便被生生打了半炷香,衣角血迹斑驳,掌心磨破,连一句“你委屈了”都没有听见。
蛮蛮从回忆里慢慢回过神来。眼前仍是那个熟悉的侧脸——夏秋华仿佛永远都那样,挺着脖子,嘴唇紧抿着,一副永不低头的模样。哪怕局势已变,众人眼神尽数落在她身上,她也还是那副傲气的样子,仿佛谁也奈何不了她。蛮蛮只是淡淡地望着,神色平静无波。
那副模样,反倒显得她像个旁观者,仿佛刚才被挑衅的人从来不是她。王夫人到底还是懂场面的,面色讪讪地站起来,低声扯了扯夏云氏的袖子,转身将母女俩带离了谢家席前。一场尴尬的戏终被强行收场。谢家祖母依旧稳坐原位,未出一言,只抿了口茶,便将目光移向别处。谢夫人与谢凌灵相视一眼,也未多言,只顺势与旁边的夫人们攀谈起来,话题很快便转到哪个世家新出的笛曲、哪家的表姑娘近日要下嫁何处,一如既往,体面、有分寸、不留余地。没人再提王夫人,也没人回头看那母女俩一眼。
至此,蛮蛮知道这场宴席之后,谢家女眷不再给她留面子,连王夫人都没能再多留半分情分,夏秋华这条路,算是走到了尽头。而蛮蛮,也终于在心底悄然划下一笔账:这一局,她赢了。她站起身时步态从容,裙摆掠过花纹青石,细细擦着余光未散的暮色,只转身悄悄去了谢绮的帐篷外。她站在帐前等着,不多时,便有丫鬟提灯而来将谢知止的批注交给她。
蛮蛮点点头,神色极安静,她低头拨了拨袖间细线,眼尾却带着笑意。接下来,就该轮到她自己登场了。